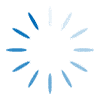沈知韫先是一愣,旋即有些诧异。她本以为,贺令昭会仗着昭宁大长公主有恃无恐,却不想他竟然直接去跪祠堂了,这倒出乎了沈知韫的意料之外。
昭宁大长公主有心想阻止,但想到贺承安离开盛京前,特地来同她说的那一番话之后,昭宁大长公主便发不出声音了。
如今既然贺令昭主动自请跪祠堂,她这个祖母也不好再多说什么,之后昭宁大长公主便让她们都散了。
沈知韫回到院中坐了一会儿,侍女们便将饭菜摆好了。
沈知韫用过饭,看时辰还早,想了想,便同青芷道:“你去找静兰,让她去厨房拿些贺令昭爱吃的饭菜装起来。”
很快,青芷就拎了个食盒回来了,然后她们主仆三人提了盏灯笼往贺家祠堂的方向行去。
贺家的祠堂俢在西北侧,虽然府中灯火通明,但靠近祠堂这边夜里鲜少有人走动,且这边遍植树木,青芷第一次来这里,心里便有些发毛。
但看了眼身侧面容平静的沈知韫,与一脸傻气的红蔻,青芷顿时心安了不少。
很快,她们主仆三人便到了祠堂。
沈知韫接过食盒,同青芷和红蔻道:“你们两个在这里等我。”
青芷应了声,立刻和红蔻挨在一起。
在沈知韫她们主仆三人到祠堂时,昭宁大长公主与王淑慧也遣了人来,不过这两拨人看见沈知韫臂弯里的食盒之后,便又悄然离开了。
沈知韫提裙上了台阶,在夜色里轻轻推开祠堂的门。
映入眼帘的,先是一片摆放整齐的牌位。牌位下是放置供品香炉的供桌,供桌旁一对成人手臂粗的白烛,将供桌周围照的十分明亮。
而贺令昭身子前倾,此刻正趴在供桌前的地上,不知道在干什么。
沈知韫掩上祠堂门,拎着食盒走近,待看清眼前的一幕,沈知韫顿时目瞪口呆愣在原地。
第二十五章
贺令昭趴的太久胳膊有些酸, 他直起身子刚要活动筋骨时,冷不丁看见身后一个人影,贺令昭顿时吓的直接弹跳起来。
再一扭头,看见来的是沈知韫时, 贺令昭这才松了一口气:“吓死我了, 你走路怎么没声啊!我还以为是祖宗显灵来教训我这个不孝子孙了呢!”
“你在做什么?”沈知韫的目光落在蒲团前散落的笔墨纸砚上。
“抄书。”说话间, 贺令昭看见了沈知韫臂弯里的食盒,他立刻高兴道,“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?”正好他饿了。
沈知韫将食盒递给贺令昭, 去捡蒲团前散落的纸张。
贺令昭则打开食盒,将里面的饭菜端出来一看, 发现竟然全是他爱吃的。
“你在抄学规?!”沈知韫拿着纸张,愕然看向贺令昭。
贺令昭一面扒饭,一面口齿不清道:“嗯,本来沈老头罚我散学后, 当着他的面抄来着,但是我今天又逃学了,正好现在没事,就抄一抄好了。”
沈知韫:“!!!”
“不是,你人都打了, 还在乎罚抄学规这事?”沈知韫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。
“这俩又不是一回事。沈老头罚抄我认我也抄, 打裴狗那事我认但我不后悔,再来一次,我还是照样打他。”
沈知韫:“……”
他们成婚到现在也两个多月了, 凭借着沈知韫对贺令昭的了解, 贺令昭不是无故会动手的人。
“今天你在太学发生什么事了?”沈知韫问。
“徐祭酒那老头过来没告诉你们吗?”
“他同婆母说了,我不知道。”
原本这种事, 贺令昭懒得再说第二遍,但沈知韫既问了,他便闷闷将今日发生的事说了。
“所以因为他破坏了你的计划,你就打了他?”沈知韫觉得,这不像她认识的那个贺令昭。
“是,也不是。”贺令昭捧着碗,恨恨道,“裴方淙那个狗东西是故意害我的。”
“这话怎么说?”
贺令昭迟疑了一下,沈知韫见状,便不再问了,而是道:“那你好好抄,我先回去了。”
“哎哎哎,你这刚来怎么就走了,你再陪我待一会儿。”说完,贺令昭不由分说拉着沈知韫的袖子,让她坐在了他的对面。
沈知韫一本正经道:“列祖列宗不是在陪你么?”
“他们只能看着我,又不能陪我说话。”
“你想说什么?”沈知韫问。
贺令昭也没什么想说的,但这个时候,沈知韫来这里见他,他莫名就想让沈知韫陪他待一会儿。所以顿了顿,他又继续起了先前的话题:“你还记得,上次你整改书房那次,我爹出了趟门,回来就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,还罚我做文章看书的事么?”
“我记得,你当时说,是因为公爹看见了裴方淙。”然后心里不平衡,就回来拿他撒气了。
“对,就是因为裴方淙那个狗东西。”贺令昭咬牙切齿道。
之后,沈知韫从贺令昭口中,知道了他与裴方淙之间的往事。
贺承安与兴昌伯交好,虽然贺承安常年待在北境,但只要一回京,他就会去找兴昌伯喝酒。而贺令昭兄弟二人与裴方淙年纪相仿,贺承安与老友相聚时,也会带着他们去裴家玩儿。
“你也知道,我小时候身体不好,我祖母不怎么允许我出门,所以我的朋友很少,除了我哥之外,就只剩下裴方淙那个狗东西了。”
“那你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?”沈知韫不明白。
“我也不知道。小时候,裴方淙那个狗东西人很好,我每次去裴家时,他都会带我玩儿,而且我闯祸我爹罚我的时候,他会立刻帮我向我爹求情。在我十岁之前,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。”
“你十岁那年发生了什么?”
“那年冬天,我在裴家玩藏猫儿的时候,被人从身后推进了裴家的水塘里。”
沈知韫眼皮骤然一跳。
贺令昭垂着眼睛,声音低低的:“当时幸亏我哥也在,是他将我从水塘里救出来的。那次落水差点要了我的命,我祖母当时发了很大的火,兴昌伯夫妇还曾亲自携了他登门谢罪,但那时候我一直在昏睡,并不知道这事。
”他是除了我哥之外,我唯一的朋友,我不想失去这个朋友,我便同我祖母说,同兴昌伯说,我落水的事跟他无关,让他们不要怪他。但过了很久之后,我才意外从别人口中听说,兴昌伯因为这事,将他打的半死。我十分愧疚去找他赔罪,他也没说什么,只让我好好养病。”
外面风吹过树梢发出沙沙的声音,祠堂供桌上的烛火被风扯的跃动着。
沉默须臾后,沈知韫问:“那推你下水的凶手找到了吗?”
“嗯,是裴家的一个小厮。”
“所以因为这件事,你和裴方淙的关系就逐渐疏离了?”
“算是也不算是。我落水之后,被我祖母勒令在府里将养,但我又是个躺不住的性子,偶尔会偷偷出门找他玩儿,但他很少见我,他的随从说他在温习功课。后来次数多了,我就不再找他玩儿了。我祖母见我情绪低落,便时常在公主府开宴,让官眷带与我年纪相仿的孩子过来。后来我认识了赵世恒和孔文礼他们,便与他们一道玩了。”
听着没什么问题。
沈知韫问:“若是这样的话,那你们二人之间顶多疏远罢了,你为何会说,裴方淙是故意害你的?”
“因为这种事,发生过很多次了。”
沈知韫:“……”
贺令昭十五岁之后,身体就慢慢好了。他时常跟赵世恒和孔文礼他们出去玩儿,有时候也会遇见裴方淙。因为裴方淙是他的第一个朋友,所以即便中间五年他们很少来往,但看见裴方淙的时候,贺令昭还是很高兴的,他甚至还热情的邀请裴方淙跟他们一起玩儿,但后来贺令昭才知道,自己有多愚蠢。
原本除了赵世恒和孔文礼之后,贺令昭还有好几个朋友。
但自从裴方淙加入之后,那几个朋友莫名就同贺令昭疏远,反而与裴方淙交好了。贺令昭虽然有点难过,但也并未说什么。毕竟朋友是双相选择,而且那几个朋友本身也有才华,他们或许跟裴方淙这样读书好的人更聊得来吧。
“但慢慢的,我发现,不止是朋友,还有很多其他的事,很多事情明明不是我的错,但最后却莫名成我的错了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有一年冬天我们约好去冰嬉的,但我在河边等了两个时辰他都没来,我不放心去找他,结果他在与友人煮酒论诗。他看见我的时候,还一脸惊诧的问我怎么来了?
“我当时很生气的质问他,既然他不去了,为什么不能派人来同我说一声,要让我一个人在河边等那么久?你知道他当时是怎么回答我的么?”
沈知韫:“他怎么回答的?”
“他只字不提我们提前约好去冰嬉一事,只当着众人的面安抚我,说若早知道我今日想去冰嬉,那他便不来这论诗会了。后来没过几日,便陆续有人说我脾气不好难相处以及当众给裴方淙难堪的事了。”
“你就没解释过么?”
贺令昭扯唇哂然一笑,自嘲道:“我解不解释也没什么区别。我品行顽劣,而裴方淙待人和善,又是出了名的谦谦君子,我与他之间,大家自然信他的话。也是那个时候,我才恍然意识到,自从再见到裴方淙之后,除了我的朋友变成了他的朋友之外,这种明明错的人不是我,但却所有人都觉得是我不对的事多了很多。”而且拜裴方淙所赐,他的名声也越来越不好了。
沈知韫没想到,贺令昭与裴方淙之间,竟然还有一段过往。
“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,就直接疏远了裴方淙,想着大路朝天各走一边。但偏偏裴方淙就跟条疯狗似的,我都已经疏远他了,他却还要时不时的来恶心我。就像这次的事,我明明知道他是在故意针对我,但他做的滴水不漏完全不留话柄,最后甚至还要顶着那张令人作呕的无辜表情来恶心我,那我就只能用拳头教他来做人了。”
所以沈怀章罚抄一事,他认罚也认抄,至于打裴方淙一事,他认但他不后悔。若再来一次,他还是会打他,并且还会打的比这次更狠。
沈知韫听完之后,皱眉沉思片刻,问:“有没有可能裴方淙是在故意激怒你?”
“故意激怒让我揍他?裴方淙脑袋有毛病啊?”骂完这句之后,贺令昭想了想,又猛地坐直身子,“不过也有可能,他脑袋是真的有毛病,不然他老像条疯狗一样追着我咬干什么?!”
沈知韫:“……”
看着贺令昭桀骜不驯的眉眼,沈知韫蓦的想起起王淑慧那张疲惫的脸。自她过门之后,王淑慧平日里一直是温柔和蔼,这是她第一次看见王淑慧这样。
沈知韫轻声问:“你揍裴方淙一顿你是舒坦了,但你可曾想过你娘?”
“这关我娘什么事?”
“今日徐祭酒来府里告知此事之后,你娘已让林管家备了厚礼去兴昌伯府探望……”
贺令昭蹭的一下站起来:“娘真是糊涂,为什么要让林叔去看他?我找娘去。”
说着,贺令昭便要往外走,沈知韫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。
“糊涂的人是你。”
贺令昭倏忽止步,继而猛地回头,盯着沈知韫看了片刻,他眼底划过一抹自嘲:“你也跟赵世恒他们一样,觉得今天的事只是个意外,是我反应太大了是不是?”
“你与裴方淙之间的事我不予置评。但世人默认子不教父之过,如今定北侯远在北境,你既在众目睽睽之下打了人,那么到最后,这个烂摊子只能由你娘来收。”说完之后,沈知韫径自往外走了。
自她嫁过来之后,王淑慧待她很好,今夜这番话,就权当她是报答王淑慧待她的那些好,至于贺令昭肯不肯听,那就非她能控制了。
青芷和红蔻待在廊下避风处说话,见沈知韫出来了,她们二人忙迎上来,然后主仆三人一道离开了。
偌大的祠堂里,便只剩下贺令昭形影相吊站在一排排肃穆的牌位下。
待沈知韫离开之后,康乐便推开祠堂的门,他原本想同贺令昭说,夜深了让贺令昭回去歇息,了。毕竟今夜这跪祠堂是贺令昭自己提出来的,昭宁大长公主与侯夫人都没罚他,所以贺令昭想什么时候回去就可以什么时候回去。
但见贺令昭立在那里,一言不发的模样,康乐便默然将话咽了回去,轻轻的又将祠堂的门掩上了。
“你怎么没问?”安平迎上来。
康乐袖着手,小声道:“二公子的情绪不太对,别上赶着挨骂,再等等。”
这一等就等到了半夜,祠堂的门还是没开。康乐不由在心里称奇,之前贺承安在府里罚贺令昭跪祠堂的时候,几乎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时辰,贺令昭就从里面出来了,但今夜都这个时候了,贺令昭竟然还没出来。
“二公子不会在里面睡着了吧?”安平有些担心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